|作者:张欣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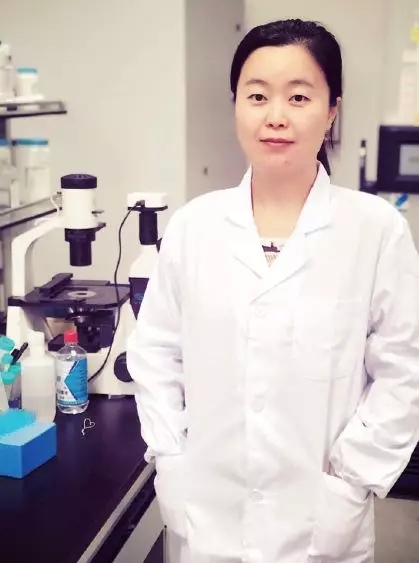
作者在实验室留影
在2018 年初的“强磁场与生命健康”的香山会议上,一位前辈提到,若是想从事交叉学科的研究,就要主动到对方的领域中去,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交叉。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直到2012 年夏天加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之后,才开始接触到物理学科。从此慢慢走上了物理和生物交叉之路。三十多岁了,才硬着头皮来学习物理,似懂非懂地读相关文献和书籍,以及参加物理学领域的各种学术会议。越来越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知识储备远远不够解释我们所观测到的实验现象。但这同时也是作为科研工作者最幸福的地方,每一天都不会枯燥,可以从大量的文献和书籍中学到新的知识,然后进行思考和推论。如果还能从实验中发现与预期相符合的现象,或者甚至是相反的,亦或是自己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现象时,那种满足、兴奋和新奇感是任何其他行业无法体会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探索,而每次不仅从实验小鼠上,也从自己、家人和朋友身上看到磁场确实能够对生命健康带来一些益处时,幸福之感油然而生,因为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问题恰好能够为医学健康提供一些理论解释和工具,而不是仅限于对纯科学的探索,那对于研究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我便“断章取义”,直接忽略庄老先生的后半句“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因为只要喜欢,就不会“殆己”。
 医学、生物、再到物理和生物的交叉 医学、生物、再到物理和生物的交叉
实话实说,中学时学到的那点物理知识,从踏进大学校园起就被抛至脑后了。1996 年我遵照家人的意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又按照家人的想法选择了基础医学而不是临床医学,因为他们认为做临床医生会接触不必要的医患纠纷,这对女孩子尤其不好。当时在母亲的脑海里,一个女孩子,在实验室里做做实验,教教书,那定是极好的。这一点不得不佩服母亲的前瞻性思维和电视剧看多了导致的幻象,而我作为一个典型中式家庭教育出来的乖乖女,自然是顺从了母亲的想法和安排。后来有时也会想,如果当年选择了临床医学,自己也一定会做个好医生。当然这也只是想想而已。如果一切重新来过,我还是会选择做科研。这并不是因为做科研像母亲当年想的那样,在实验室里待一待,没事儿写写书,带带学生就好了。在现实中,科研工作者不仅要接受从物质角度来讲很低的投入产出比,还要习惯于失败的实验远远多于成功实验的事实。但是偶尔成功一次,那种精神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却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
2001 年本科毕业后我去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大学学的是非常基础的细胞生物学。我所在的印第安纳大学Bloomington 分校是一座非常美丽安静的大学城,有一群很质朴单纯的人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学习和生活。多谢当时的导师Claire Walczak 和其他学术委员会成员,让我踏踏实实地打好了科研工作者应该有的基本科学功底,养成了日后让自己受益终生的一些好的科研习惯。2008 年我去了哈佛医学院/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当时的导师Ulrike Eggert 是一位刚独立没几年的女导师。她是学化学出身,需要一个学生物的来做化学和生物学的交叉研究,想看一些新的小分子化合物在细胞里的作用机理。所以作为当时实验室里第一个生物医学出身的博士后,就在那里跟一些化学出身的同事们学习了好几年。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发现学科交叉比传统的生物学更有趣。但是说实话,当时并没有真的做太多,我也曾努力试图学习了化学,觉得太难了,自己动手做化学合成不仅要在别人帮助下,而且笨手笨脚很久都搞不好。最后就干脆与人合作,一起制定实验计划来共同完成。现在想想这其实也是学科交叉的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把各自的强项联合起来,而不是每个人什么都会做。
2012 年我和爱人在朋友的召唤下加盟强磁场中心,主要是想做“磁生物学”,结合之前的医学和生物背景研究磁场对生物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由于多方面原因,在2012—2015 年期间经历了极其痛苦的“转型”。一是因为没有现成的实验条件可以直接利用。强磁场中心的磁体当时很多还没有建成,更重要的是,已经建成的几个磁体都是用来做物理和材料研究的,不能直接用于研究脆弱挑剔又变化多端的生物样品;二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文献中有关磁场生物学效应的虽然不少,但总的来说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实验结果看上去五花八门,难辨是非;三是实验室建立初期,作为生物医学背景的人加入以物理和工程为主的研究所,平时的讲座报告说实话连题目都看不懂,更重要的是做生物医学实验的设备缺乏,除了一起回国的几个朋友间可以互相借用仪器外,其他实验条件都要从零开始准备。所以在这3 年间,对我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导致没有文章也没有关于磁生物学方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除了拿到了一个关于传统的细胞生物学方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幸好有单位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一起回国的朋友们的帮助(免费使用他们的仪器并在我们实验室青黄不接时借给了几万块钱应急),还有实验室学生和工作人员一起的咬牙坚持,熬过了最初的3 年。我们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分析,找出了一些模糊的规律,然后设计了一系列实验进行验证,还跟做仪器技术出身的同事陆轻铀一起进行了尝试,把溶液扫描隧道显微镜在各种生物样品上进行测试,摸索出可以进行生物样品扫描的方法,得到了近生理状态下的蛋白单分子高分辨率图像,然后进一步验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猜想。另一方面,在强磁场中心自制的一系列大磁体上,与工程部的同事们合作搭建起一套适合研究生物样品的平台,可以研究多种细胞以及实验动物等等。几年下来的知识和实验积累,让我们看到了磁场对肿瘤的抑制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将其中的机理、磁场参数等等研究清楚,大胆推测小心验证,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将磁场有效安全地应用于肿瘤治疗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验室的学生们也对磁生物学越来越感兴趣,并联合国内外做磁生物学和磁性纳米材料等方面的诸多老师,例如西北工业大学商澎老师和东南大学顾宁老师等,大家一起讨论项目和科学问题。在多位前辈的支持下,举办了包括香山会议等一系列磁场和生命健康相关会议,使磁生物学这个本来比较冷门的边缘学科开始看到曙光。现在,我们也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双管齐下,不仅要从根本上深度发掘磁场影响生物体的物理机制,也要同时探索将磁场应用于肿瘤治疗的方案和可能性。在这两方面,我们最近都获得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进展,希望在未来的几年能以成果的形式向公众展示。
 一路遇恩师 一路遇恩师
想想自己真的很幸运,这么多年来,遇到的全都是超级好的老师。本科毕业设计时我跟随的是童坦君院士课题组的毛泽斌老师。当时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接触童院士,但是至今都记得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要读几个小时的文献。毛老师教了我一些基本的分子克隆等实验技能,他说这样的话就能在任何生物医学实验室里有用武之地。
后来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又先后遇到了几位老师,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我的博士生导师Claire Walczak。她热情豪放,爱美爱生活,同时学术上极其严谨,儿女双全的她让我看到了自己以后想要成为的样子。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博后阶段和回国之后,在学术会议上遇见时还是会开心地约饭,拥抱时还是会热泪盈眶,她甚至会把我的孩子扛在她的肩头, 笑称孩子应该叫她grandma,就为了让我能腾出手来趁热吃饭。每次想起Claire,心头都是暖暖的。
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个德国人,Ulrike Eggert,她性格内敛,内心仁厚,认真严谨,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曾经在几年内都是我们BCMP系里唯一的女教授。在高手如云的哈佛医学院里,她总是保持着云淡风轻的样子。从来没有见过她大声说话,也没有跟谁红过脸。博士后几年间在科研和生活两方面都给予了我极大的自由和支持。后来她决定和丈夫一起回欧洲时,也充分尊重了我的意见,让我留在波士顿继续做自己想要完成的课题,并且把我和另外一个土耳其博士后一起托付给了她的博后导师,美国科学院院士Tim Mitchison。
Tim 曾笑称我是他adopted postdoc。是的,在他实验室里待了一年多,每次跟他讨论都能收获满满。后来朋友拉我们回国时我有些犹豫不决,去咨询Tim 的意见,他说他很看好中国,觉得我们的国家在走上坡路,所以我应该回国试试。在我们到合肥不到一年时,他还来到强磁场中心,看看我们在这里做的怎么样,并且向我提出了关注磁场对微管细胞骨架影响的建议。当时我的心里非常没有底,也正处于一开始的“艰难黑暗期”,对于新的领域充满了迷茫,不知从哪里下手,也担心自己从零开始学习物理会不会太晚。Tim 说起自己也是三十多岁才开始自学化学,只要肯干,从头开始学物理没那么可怕。他的话燃起了我的熊熊斗志,便开始向强磁场中心的一些老师请教问题,也很幸运遇到了好几位耐心的同事,不厌其烦的向我科普,同时也促进了相互间的一些合作,包括前面提到的与陆轻铀的合作。后来在美国的一个学术会议遇到Tim时,他说非常喜欢“科学岛”,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希望能够再去看我们,也很高兴我们能在那里工作。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几年前Tim 为我写推荐信时,评价我是哈佛医学院博士后里面的top 5%,非常适合做科研。对此我内心其实非常惭愧,因为自己并没有达到他所说的水平,但同时也非常感激他看好我,希望能以此鞭策自己去达到更高的目标。
回国之后,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们都很支持。例如我们院长,为人谦和包容,给予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八十多岁高龄的张裕恒院士也给了我们莫大的支持,并从他的角度给我们的研究提了很多宝贵意见。还有一些虽然不是同一单位但却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的沈保根院士、商澎老师和顾宁老师等,他们让我看到了前辈们对后辈的期望,以及对我们这个新兴领域的支持。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作为女性科研工作者,永远没法绕开这个话题。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怀揣着热乎乎的结婚证和offer 一起去了美国读博。读博期间和博后期间有了大女儿和小儿子,现在分别是14 岁和9 岁。做母亲后深深感悟到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就算尽力减少个人睡眠和娱乐,但是女性的工作时间还是不能与同在领域“厮杀”的男性PK,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能做的就是想办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方法。经过多年的挣扎和摸索,我个人觉得有三点比较重要,在此抛砖引玉。

作者幸福的一家
首先是时间上的调整。有孩子前我和我爱人都是整天泡在实验室,但有了孩子后,作为母亲很难再做到这一点了,我就尽量晚上和周末不去或者少去实验室。把上班的时间提前一点,下班的时间推后一点,再将实验记录、数据分析、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等尽量带到家里做,这样就可以把在实验室的时间全部用来做实验。周末偶尔去实验室也可以带上孩子,推着小推车走在路上就把孩子哄睡着,之后趁机专心做实验。当然小孩中途醒来的状况时常发生,这时候就只能考验自己的应变能力了。另外,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清晨4 点左右起来工作,早上很安静,头脑也很清醒,所以效率会更高。
其次就是练就了任其环境如何,我自岿然不动的能力。具体来讲就是可以迅速在任何地方进入工作状态,从室内游乐场边的小破桌到孩子兴趣班旁的咖啡馆,从高铁到飞机,都是可以打开笔记本电脑工作的地方。如果环境实在太嘈杂,就干一些零碎的不太需要集中思考的工作,例如填那些无聊的表格,或者是给文章做图等。我发现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但这一点在我看来非常必要。零散的时间尽量都利用起来,积少成多,滴水成河。
最后就是尽量接受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我生2 个孩子一共加起来休了2 个月的产假。每次都是月子一满就飞奔回实验室。这一切的一切都要衷心感谢双方父母所给予的坚强后盾。因为不愿让孩子离开我们,于是我的母亲和公婆前前后后多次赴美帮我们带孩子,不辞辛苦,毫无怨言。幸运的是,回国后公婆和我们长住,尽心尽力地帮忙,既帮助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工作,同时一家人也能天天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但是即使是在老人们的无私帮助下,如今来自学校教育体系的对家长们的各种要求,我们也是无法做到和别的家长看齐。所以就只好做那种对孩子进行放养式管理的佛系家长。但换个角度来看,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正是对孩子更好的教育吗?他们看到了爸爸妈妈一直都在努力工作,在逐渐长大后,孩子们自然而然越来越努力,越来越自觉了。
 后记 后记
受邀在“三·八节”写专题文章,其实内心非常忐忑,因为面对太多比我优秀的女性科研工作者,自己才疏学浅,实在是班门弄斧。但是本着言之有信的原则,就试着写一点自己的体会吧。想起来前段时间在凝聚态物理会议上作报告,一位学物理的女生跑来很真诚地对我说“我太喜欢你了!”还有一位物理系男生决定转行报考我们课题组,说他就是想从事物理和生物的交叉研究。这两位年轻学生让我很感动。仔细想想,从事科研行业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许我的经历能够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在科研和家庭间的平衡有一些帮助,或者能令对交叉学科感兴趣但心里又没什么底儿的年轻人有所启发,这就足够了。虽然大多数女性对工作的投入时间会被家和孩子分走一部分,但是和睦幸福的家及孩子们对母亲的爱,同时也是我们的充电宝和加油站。让我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生风,保持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科研的热爱,相信“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踏踏实实地在科学的海洋里遨游和探索。这份简单的幸福又岂是其他行业的人所能体会的?
本文选自《物理》2019年第3期
|